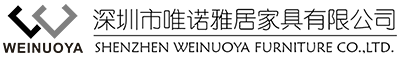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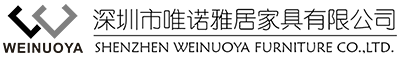




发布者:沙发 发布时间: 2024-05-27 06:11:47
4月25日,第十四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大师班“国族史诗与心灵奇迹”在京举行。本届北影节“天坛奖”评委会主席、塞尔维亚导演埃米尔·库斯图里卡作为主讲嘉宾,同中国导演黄建新、作家余华展开对谈。
1954年出生在南斯拉夫萨拉热窝的库斯图里卡,今年就将年满70岁。作为前南地区的演员、编剧和导演,他在中国观众熟知的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中曾客串过游击队员而初登大银幕。上世纪80年代后,他正式拿起导筒,先后拍出了《你还记得多莉·贝尔吗?》《爸爸出差时》《流浪者之歌》《亚利桑那之梦》《地下》等多部脍炙人口的影坛佳作,令他在欧洲三大电影节上斩获颇丰,成就了“全世界最会得奖的电影导演”之名。
“人是如何感受历史中那些巨大灾难的呢?又是怎样度过那些灾难的呢?无论是在灾难前还是在灾难后,遗忘始终居于统治地位。”恰如库斯图里卡在个人自传《我身在历史何处》中所说,他总是用影像讲述着一个失去的国度,一段无法重温的乡愁,以及那个在历史长河中被迫止步不前的南斯拉夫。对谈开始前,一段混剪的视频为现场观众捡拾起过往他在电影创作中“绝不向遗忘屈服”的努力与挣扎,初心和抗争。
“《地下》是我看到的第一部库斯图里卡导演的作品。”黄建新导演在发言时回忆说,“当时是一位朋友向我推荐的,说电影的风格太独特了。那时找不到资源,不知是从谁那里借到了录像带,我连夜看完,呆坐在沙发上长久没动地方,带给我的冲击太大了。”
“电影讲述了在大时代的背景下,一个国家从被占领到解体、分裂,把民族心灵史同一对兄弟间的故事结合在一起。库斯图里卡导演用一种自由的畅想,塑造了一众狂放不羁的艺术形象。现在我们说他的手法是魔幻现实主义的,恰在那段时期,我的一些影片也采用了非写实主义、表现主义的方法。而且由于历史原因,导演看待他的国家的历史,同中国的历史间也有一些关系,在意识形态上存在一些关联和反思。所以看《地下》,包括之后看《爸爸出差时》都会让我作为中国观众产生很多联想,可以说他的电影超越了文学、超越了艺术,带给我们更多在人类意义上广泛的想象。”黄建新说。
余华在介绍自己对导演片单的阅片史时,亲切地将库斯图里卡称为“老库”。“我看老库的第一部电影是《爸爸出差时》,是在一位中国导演的家里,他从国外带回的英文字幕录像带。我听不懂里面的台词,却看懂了。因为我和黄建新一样,都经历过那个特殊时代,所以不需要翻译也能看懂电影的故事。《地下》我是用VCD碟片看的,《流浪者之歌》在从网上下载的,只要能找到片源,老库的电影我基本上都看过。”
“今天大师班的题目‘国族史诗与心灵奇迹’,起得特别好。老库的电影中呈现的南斯拉夫,剧情中人物的经历,那种国族创痛感并不是当下中国人可以体会到的。其次他的电影可以说展现的就是心灵奇迹,那种天马行空、不拘一格着实令人震撼。”余华说。
库斯图里卡表示自己的电影创作,是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1981年,我拍了个人第一部剧情长片《你还记得多莉·贝尔吗?》,当时南斯拉夫还是一个处在风雨飘摇中的整体。电影展现了我们在特殊经历下的一段伤痛的回忆,也反映出当时社会出现的新的情态。”
“对于南斯拉夫来说,在战乱之前它还是一个非常好的国家。非常不幸的是,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它的内外冲突都特别尖锐。作为电影工作者,我是幸运的,那段经历给了我创作的灵感,但我们的人民则大多没有这份幸运。”库斯图里卡表示直到上个世纪末,历史的创痛也不曾在自己的心灵中减轻。“但与此同时,人们在苦中作乐产生出的幽默感也影响了我的创作。我也希望可以借由这样时代背景的展现,更好地把个人的家国情怀放入电影,比如我从小怎么长大,我的求学经验,我的价值观等等一路成长的过程和经历。”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怎样用电影更好地参与到这样的世界当中,把我们的故事放到大银幕上,让其他国家的观众也能够产生情感上的共鸣。电影带给我们的经验就是如此,它一定能够引来一群志同道合的人走进电影院,并且去相信电影中呈现的东西并不过时。我不过是用艺术的形式,把更多的魔幻现实主义和超现实的东西融入进去,让大家理解人们遭受到的苦难,无论是身体上还是心灵上的。”库斯图里卡说。
“我特别同意库斯图里卡导演的观点,你所经历的一切事情一定会在你身上留下深深的烙印和痕迹。当你真诚地去反映这些事情的时候,你的想象力、你的表达方式自然而然也就产生了。对艺术家而言,这是非常宝贵的经历。总的来说,谁也逃不掉历史对他的影响。每个导演会有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偏好,但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关注的不是一个单一的灵魂,我们看到的、表现的其实是一个真实的、多级的、丰富的灵魂,来自那样的人,那样的群体。如此,我们的影片也好,小说也罢才会有比较长时间的价值,才有它的生命力。”黄建新说。
对线年,陈凯歌拍了《霸王别姬》,张艺谋拍了《活着》,我拍了《背靠背,脸对脸》,三部电影都来源自小说。其实我的前六部电影,五部都是源于小说。我一直认为在中国,作家比电影人在观察人性、塑造人物方面要强,他们在写作时可以进入一种冥想状态,而电影则是现场集体创作,作家更能触摸到社会的脉动和本质。”黄建新表示,电影人的创作一定会同他的人生经历有关,“当我可以拍戏的时候,我就特别关注普通人的遭遇。评论界曾把我的电影视作先锋,后来我去澳大利亚做访问学者,看了很多纪录片,回国后我的电影开始向写实主义转向,想记录下中国改革初期的变化。《红灯停,绿灯行》(又名《打左灯,向右转》)中的主场景就是我小时候成长的院子,拍完后一个月那个院子就拆掉了,我把它保留在了电影中。”
相较于黄建新导演的条分缕析,作家余华的发言则显得随意家常。“我和老库小时候都是‘坏孩子’,小时候想干什么干什么,我读书时的教室就像个菜市场。老库在《我身在历史何处》中也写到,当年的玩伴都进了监狱,他要是不拍电影,肯定也进去了。所以是艺术和电影救了库斯图里卡,把他变成了一个伟大的艺术家。老库现在住在贝尔格莱德,但他成长、上学都是在萨拉热窝,我去过萨拉热窝,专门去看了他从小长大的街区。站在路边,我就想,这哥们小时候干过的坏事一定跟街上来来往往的车辆一样多,所以我特别推荐大家去看看他的自传。”
余华还饶有兴趣地回忆了他和“老库”的第一次见面,是在贝尔格莱德萨瓦河畔的一个公园。“我们在那吃了晚饭后,他就告诉我说,走,带你去看看我拍《地下》的灵感是从哪来的。我注意到他的鞋带没系好,还提醒他,他嗯了一句,然后继续走路,后来我发现不系好鞋带是他的一个习惯。他把我领到了一处下沉的遗址,里面有一个小门。当时灯光是照在下面的,周遭一片黑咕隆咚。我一下子就明白了,为什么那么多人有过他类似的经历,却只有他可以拍出《地下》,是历史选择了库斯图里卡看中了那个小门。”
“在我看来,老库心里住着两个灵魂,一个是莎士比亚灵魂,一个是契诃夫的灵魂,这两个灵魂有时候是分开的,有时候又合在一起。比如说他拍《爸爸出差时》时,是契诃夫式的灵魂(在主导);但是你看《地下》的时候,会感觉到他那莎士比亚式的灵魂蹦出来了,那种放肆、那种开放、那种为所欲为、天马行空,所有这些都出来了。到了《流浪者之歌》,你又感觉他那两个灵魂又合在了一起。所以他是这样的导演,他的作品是他的灵魂碰到了什么,然后他就去创作什么,反而跟时间的关系不是那么紧密,包括他后来风格的转变其实也跟时间的关系不大。”余华说。
余华的发言让库斯图里卡莞尔一笑,“大家现在看我的鞋子,鞋带就没有系上,为什么没系?因为我现在心情特别平和,如果我在街头受到威胁,有人要打我,我就会系紧鞋带,随时准备逃跑。”
“说到小时候的顽劣,其实我出生在一个家境不错的家庭,但我周围的人家有单亲家庭,有的家庭比较贫困,有的家庭里还有罪犯。在我的记忆里,我一直想寻找他们那种家庭的存在感,而且我也一直在寻找这种力量。在我的电影中有不少街上的人、流浪者,他们也见证了社会的变迁。作为一名导演,你要能够看到社会上到底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并且能够把现实剥离出来。”
“我的电影创作开启于半个世纪前,这期间我活了下来,成了艺术家。我来自南斯拉夫,也见证了柏林墙的倒塌,我希望能够用电影镜头,来展现时代和家国的变迁。同时,我也看到了社会的很多变化,在我看来,未来并不是暗淡的,我们必须要适应社会的变化,才可能去预见未来、畅想未来。”库斯图里卡还特别提及,自己想在中国创作一部电影,“片名叫做《成吉思汗的白云》。”
“这个剧本老库已经准备好多年了,改编自艾特玛托夫(吉尔吉斯斯坦作家)的同名小说。我读了剧本后觉得写得好极了。”余华补充道,“在成吉思汗那么强悍一个大人物身上,老库却想从他人性的某一种脆弱的角度切入进去,这有点像当年他带我去看创作电影《地下》时灵感的出处,那个小门一样。我觉得越是强悍的人物,他最脆弱的一面才是他人性中最打动人的地方。期待这部电影能早日在中国开拍。”
大师班上,库斯图里卡还介绍了自己拍摄电影的经验。“对于挑选演员,还是要找到他人性或者是性格的一面。有时候作为导演也可以从演员的性格中进行想象,观众已经记住了某位演员的脸孔,但我却觉得是不是可以为他塑造其他的形象让你记不住他的脸呢?我在选角的时候往往会做一些视觉上的创意工作。”
“在拍摄的时候,比如拍河边、草地上的场景,我会坐在那,拿一杯咖啡静静地看他们的表演。如果演员有些紧张,我会试图同他一起放松下来,他要是还放松不下来,我就会建议,干脆我们一起跳到河里怎么样。拍摄《爸爸出差时》时,里面饰演爸爸和爷爷的演员都是群众演员,并没有什么表演经验,我就让他们更多地用自己的想象力去呈现。”
“作为导演,我们其实也是翻译,把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翻译成荒诞和怀疑的电影语言和电影故事。电影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现在还有一个趋势是人人都可以拍电影,但我认为电影制作依然是要有一颗匠心。电影是一个非常具象的存在,我们通过在大银幕上讲电影的手段,来跟时代产生共鸣或者产生连接。”库斯图里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