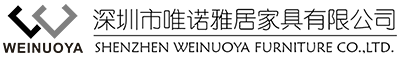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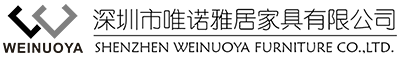




发布者:柜架 发布时间: 2024-08-19 02:00:55
本文所称的赣南,地理范围有今天的赣州和吉安两个地级市,闽西主要指龙岩地级市,即从前的汀州地区。潮汕移民进入赣南、闽西,以清初、抗战两个时期较为典型,前者和郑成功部队被清政府招安有关,后者则源起于抗战时期潮汕的大饥荒。1949年后,有支援所谓“三线”建设,一部分潮汕人移民赣南、闽西。移民赣南、闽西的潮汕人处于强势客家族群的包围,有的后来选择回归潮汕,有的被客家族群同化,但也有个别潮汕方言岛保存。
从前韩江联系赣、汀、梅、潮诸州,经济因素使得一些潮汕人进入赣、汀两地做生意,甚至成立潮汕会馆。“韩江是水上交通主动脉,既是粤东和闽西南的交通纽带,也是潮汕和赣南的文化纽带,对推动潮汕文化的演变作用重大。”[1]
广东潮汕航运的开通,在汀州的商业贸易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汀江是贯穿闽西客家地区的水路大动脉,号称“天下客家第一江”。汀江源于汀州长汀、宁化的崇山峻岭之中,流经长汀、上杭、永定,再入广东境内与梅江汇合成韩江从潮州出海。汀州的食盐从福州经闽江起运,闽江滩流险峻,水路运输十分艰难,加之闽江不能直达汀州,必须中途上岸后,再由人力肩挑长途跋涉,往往当年的食盐要到第二年才能运到汀州。加上奸商操纵,从中盘剥,盐价十分昂贵,汀州百姓怨声载道。宋绍定五年,汀州知州事李华、长汀县令宋慈请求“更运潮盐”,经核准后,汀州的食盐便从潮州水路运来,这样快速缩短了运盐的路线和时间,打击了奸商,降低了盐价,造福于汀州百姓。[2]
可见,早在宋代,汀、赣、潮在经济上慢慢的开始走向一体。而韩江及其支流起到重大作用。“汀州至潮州水路运盐路线的贯通,直接沟通了汀州和广东的商业贸易往来。汀江航运日趋繁荣,每日往来的商船达数百艘之多。汀州城内的济川桥畔形成重要的汀江运输码头。广东来的货物从这里上岸,一部分运往汀州各县,一部分经汀州中转运往赣南,而江西省和汀州各县木材、毛竹、纸等土特产也从这里装船源源不断地运往广东。汀州成了闽、粤、赣三省物资集散的重镇。三省的商人纷纷在汀州设铺开店经商,手工业作坊大量涌现,使汀江边上形成了庞大的水东市。”[3]从这段记载发现,赣南和潮州的经济往来,往往经过以汀州为中心的闽西。
古潮州为粤东、闽西、赣南的土特产集散地,其中尤以竹木土纸居多。清末,清政府在潮州城东门外设有一个征收土特产税的关卡,称为“东关府税厂”,规定韩江上游的土特产,必须先向税卡报关纳税,才运进城运往下游一带营销。因此,东门外的市场更活跃。潮州竹木多来自福建上杭、武平和江西寻邬、瑞金及广东平远、蕉岭、大埔、梅县、丰顺等地,经潮州运销于韩江中、下游一带。是时,潮州竹木市场主要聚集在两个地方。一是潮城之南,一是与潮州城北堤对峙的意溪。当时,在潮州城南门古一带,开办的竹铺就有40多家,被称为竹铺头。土纸主要产自闽西一带的长汀、连城、上杭、永定、龙岩、武平、和平等地,沿韩江水运至潮州,最多时每年达篓纸5 000担、福纸300块以上。其中大部分转销往安南、老挝、柬埔寨、香港、新加坡、槟榔屿和南洋群岛一带。民国元年至十九年(1921—1930),潮州已有篓纸行8家、福纸行10家、纸铺40家,大抵集中在府城靠东侧的东平路、太平路、东门街、开元路、西马路、水平路一带。[4]
笔者不能确定上述从事竹木、土纸的店铺到底有多少家属于客家商人所有,但大批赣南、闽西客家商人在潮州经商是不争事实。也要看到一个事实,潮客的人员流动,以客家商人进入潮汕为主要,毕竟商业活动是以潮州为中心,近代又以汕头为出口港。肯定有一些潮汕商人深入到闽西、赣南地区。闽西会馆出现证明相当数量潮商出现在汀江流域。假如没有大批潮商,会馆设置不太可能。
潮汕人在闽西汀州、峰市等地设立潮州会馆,其中汀州有两座潮州会馆,峰市也有义安会馆。以这些会馆为中心,潮汕人在当地形成势力。有人认为,会馆可以按参加者的身份分为三类。第一类以官吏为主的会馆。它们是同乡的官员、士绅和科举士子居停聚会的场所。第二类是士商共建的会馆。大体上发起创立者以官员居多,出资兴建者以商人为主。这些会馆的控制权往往在官员手中。第三类是由商人建立并控制的会馆。[5]潮汕人在闽西设立的上述三所会馆属于商人建立并控制的会馆。
潮汕人进入闽西的大规模移民潮出现在抗战时期,和1943—1944年的大饥荒有关,以潮阳为例,“民国30年,日军入县城,残酷地烧杀掳掠,百姓被杀害或被迫流离失所,人口骤减。民国32年本县发生百年未遇的干旱,灾荒助长了疫病(霍乱)的蔓延,大批人民饥病交加致死或流落异乡。据民国34年复员后的调查,战争期间全县死亡233 104人,其中受敌祸死者98 724人。至民国35年,全县剩176 993户,811 632人,比日军侵潮前的民国29年减少210 907人。”[6]
“据不完全统计,当年最终到达闽西的潮汕难民大约在10—12万人之间。”[7]20世纪60年代初期,闽西是三年因难时期的重灾区,潮汕地区要好一些,人们都倒流前往寻求生路。1961年2月20日,因交通原因在峰市滞留的有四十多个妇女,都是前往潮汕寻亲的。她们大都不识字,不会讲普通话,所讲的是一半潮汕音、一半闽西音的特殊语言。[8]以下是当年逃难至闽西的部分难民情况表:
约在2018年起,潮汕电视台断续对历史上的失散潮汕人进行系列报道,帮助失散的潮汕人后代寻亲,针对主体是抗战后期进入客区的潮汕儿童。在此引用汕头电视台的一则典型报道的大意: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日军的侵略以及接踵而至的大饥荒,迫使数以万计的潮汕人离开亲人、离开家乡,流落到兴梅、闽西、赣南各地。基本能确定,当年逃难往赣南的主要是走陆路,往闽西的主要是走水路。当年潮汕难民“走日本”的逃难之路,实际上就是粤东和闽西、赣南之间的传统商贸之路。
魏阿妹老人就是当年的潮汕难民之一。她落户到上杭已有七十多年了。她记得,她是17岁那一年离开澄海上华的。走的时候,魏阿妹是自愿的。此前,她已经眼睁睁看着自己三岁大的妹妹饿死在家里。为了活命,她随人贩子步行到留隍坐船。沿韩江溯流而上,第一站就是丰顺的留隍镇。船只一路上行,来到三河坝,汀江、梅江和梅潭河在这里汇合。逃难至此的潮汕难民也将在这里分道扬镳,或者循梅江前往丰顺、梅县,或者沿汀江继续北上,前往大埔方向。
一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茶阳还是大埔县治的所在。当时,茶阳的码头四周聚集着大批难民,正等待着命运的选择;也就是在当时,福建连城的黄文贵第一次来到大埔,想要从乱世的人口买卖中赚点钱。这是黄文贵做的唯一一次人口买卖。在这里,黄文贵带着他买来的女孩返回福建连城,而魏阿妹也在这里坐船离开了大埔,进入福建永定境内,最后在峰市的码头靠岸。上世纪九十年代,棉花滩水库建成,魏阿妹当年上岸的码头,就被永远淹没在水库下方了。这一个地区曾经是汀江水路上最大的商贸中转站。[10]
进入闽西的潮汕难民的主要迁移路线是:“丰顺留隍—大埔三河坝—大埔茶阳—永定峰市”,由峰市可沿汀江上溯至武平、上杭和长汀,也可由峰市走陆路进入永定县城和连城。
笔者实地调查,也发现历史上潮汕人进入闽西的很多。举例,2017年夏天,笔者在龙岩永定调查,中午随便找一家路边的农村饭店吃饭,店主是一位六十多岁的土生土长的客家人。得知笔者来自饶平县黄冈镇,对方提及,他的母亲来自饶平黄冈,母家在地方俗称“东前宫”。不过,这位客家人只会听、不会讲潮汕话。虽然他的母亲是潮汕人,他本人不具备潮汕人意识。他的母亲早就过世,估计最先是抗日战争期间流入闽西客家地区的儿童。另外,对方提及,从前饶平人流入永定的极多。饶平人口中,有四分之三是潮汕人,四分之一是客家人。饶平的潮语族群和客家族群进入永定是不少的。
如果说潮汕人进入闽西和经济活动有关,进入赣南的潮汕人则和战争引起的土地荒芜、人口减少和饥饿联系。潮汕地区农业环境较为优越,但长期人多地少。导致潮汕移民进入赣南地区的因素,和当地人口少、荒地多有关,原属郑成功集团的潮汕籍军人的移民江西就属这种情况:
“三藩之乱”后,江西人口锐减(有研究表明:顺治年间的战乱及“三藩之乱”中,江西死亡人口超过600万),土地荒废,清廷不得不大规模招垦,并将招垦多少作为地方官吏升迁的标准。而此时粤东、闽西这两个客家聚居区正人多田少,加上清初的禁海政策,粤东、闽西的人口大规模迁入江西赣南山区、赣中及赣西北和赣东北山区开垦。[11]
谢重光研究指出,明中叶后客家人曾倒迁入赣,其中一种形式是,“明郑旧部降清后被安插于兴国、赣县等处屯田。这部分明郑将士,有原本来自闽西、粤东北的,他们追随郑成功抗清,其中有半途叛郑降清的,有追随郑氏入台复于清廷后被遣回原籍或安插他处的,遣往兴国、赣县屯田,是其安插方式之一。”当然,明郑旧部也有不少闽南和潮汕的福佬人,他们到赣南屯田后,有的保持了自己的方言和习俗,赣县和兴国至今尚有若干闽南方言点,有的则与客家人融合,日久被同化为客家了。[12]
葛剑雄研究兴国人口也发现,“明代人口的自发迁入并未改变当地人口稀少的状况。清代前期,兴国县就成为政府组织移民的地方。最初的移民人口是政府安插的投降的郑成功旧部。……抗清失败的郑成功旧部不象其他的明朝军队那样编入,而是遣归农村。除了安置在赣南兴国县的一部分军人外,还有一部分被安置在河南省的西南部地区。”[13]针对赣县情况,“清代的赣县比今天赣县为大,它包括今赣州市郊的6个乡镇。从地形上分析,今天赣州市郊的6乡镇与赣县中部河谷丘陵区的地形相同,因距赣州城近,在明末清初的战乱中,人口大多死亡,因此也成为战后移民之所。”[14]
限于资料,难以确定清代进入赣南的潮汕人有多少。潮汕人进入赣南的第二波移民潮出现在战期间,也是潮汕人进入江西的规模最大移民。因为饥荒,大批难民经过梅州,再进入江西南部。有人又称这股避难潮为“走日本”,和日本侵略有关。“民国32年初,饥民开始大规模向粮产丰足之江西逃亡,先后逃奔江西人数虽无精确统计,估计约在十万人以上,皆系徒步经兴梅、平远进入赣境,抵筠门岭之后,经济情况许可者,可乘民船顺流至赣州、泰和等处。”[15]当年因饥荒外逃至客区的潮汕人及后代很多,不少潮汕人当时到江西客区只有几岁,但笔者不同意电视台经常用“拐卖”指代到达客区的小孩,因为当时是战争环境,不少家人主动将孩子送人,或是低价卖掉,这是不得已的求生做法。在此引用其中一则典型报道的大意:
江西赣州的马坡岭,就是当年潮汕难民“走日本”的一个重要的落脚点,现在在这里,潮汕人一样能听到亲切的乡音,体会到亲切的乡情。侯筱芳随口唱起的潮州歌谣,是她从小就听着奶奶、妈妈唱的。对于远在广东的家乡,在赣州出生的侯筱芳,有的只是非常模糊的概念。
今年92岁的兰眼亲,对于家乡,跟侯筱芳有着不一样的感情。14岁那年,兰眼亲随父母从揭阳逃难到赣州龙南。逃难路上,兰眼亲失去了父亲和姑姑,17岁的时候,她出嫁来到了马坡岭,当时,这里已经是潮汕难民的最主要的一个聚居地。
来到马坡岭的时候,许茂传已经有8岁大。最初,他父亲三兄弟带着他一路逃难,到了井冈山边上的泰和县,半年后才折返来到赣州县城,才最终安顿了下来。
没有人清楚计算过,当时赣州城外聚集的潮汕难民到底有多少?如今马坡岭一带,车水马龙,难民们搭起的草棚,几经变迁,仅剩下这一片棚户改造区,还依稀可以可见难民们生活的艰难。那么,当初又是什么原因,让这些潮汕难民可以在这里安顿下来的呢?
今年94岁的章荣有逃难的时候,是一个人上路的。到了赣州,他发现,虽然还要四处讨饭,但死亡的威胁终于解除了。位于赣州市郊虎岗山的中华儿童新村是1942年6月建成的,这是蒋经国主政赣南期间兴办的,主要是收留难民儿童,蒋经国自任村长。章荣有因为超龄,进不了儿童新村,只能到难民所接受救济。1939至1945年,蒋经国主政赣南,推行所谓“新政”,颇有成绩,同时在难民救济上,也采取了一定的措施,难怪众多潮汕难民会最终选择在马坡岭落脚,但对于难民们来说,要在当地立足,单靠救济是不够的。[16]
马坡岭位于今天赣州市章贡区赣江街道。当年的潮汕难民进入江西,主要沿“梅县—平远—寻乌—安远—赣县—泰和”一线移动。平远今属梅州,寻乌、安远和赣县今属赣州市,泰和今属吉安市,泰和成为江西省接纳潮汕难民最多的县。“赣北沦陷后,赣州为斯时江西最大商业城市,泰和则系江西战时省会,故难民均以此两地为目的地,尤以到达泰和之人数最多,先后不下六七万人。有一部分再自泰和转往吉安、吉水、遂川、兴国各县。民国33年赣中战事逆转,吉安、泰和、遂川、赣州相继陷落,难民从事垦殖者,不得不仍留居原住地,非开垦之难民,则多数随政府播迁至宁都、兴国、于都等处。”[17]
大批潮汕难民移入泰和,和当时泰和成为临时省政府所在有相当关系,泰和相比江西另外的地方,在战时环境中条件较好:
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五日,九江失守,江西省所属机关、学校开始陆续往赣中、赣南搬迁,一九三九年三月,日寇由万家埠过安义、奉新、高安等线,沿公路抵达西山万寿宫,从乐化、张公渡进攻南昌。二十三日,省政府主席熊式辉由重庆赶回南昌,下令总撤退,省会迁往泰和。临时省会地盘以县城为中心,西自苏溪,东至沿溪渡,南至冠朝,西北到三都南冈口。迁来机关、学校,企业和事业单位达数百个,一时人口猛增。如省政府驻上田萧家村,省党部驻县城老考棚,省临时参议会驻马家洲高田村。[18]
还要看到,抗战时期的赣南,治理相比中国另外的地方要好,故能吸引大批潮汕人前来。在抗战期间,蒋经国曾出任江西省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专员公署就设在赣州,下辖十一县。“战时的赣州,在蒋专员的领导下,一片朝气蓬勃,建设新赣南,列了三年计划,有五大目标;就是人人有饭吃,人人有工做,人人有屋住,人人有衣穿,人人有书读。三年以后,计划完成,街上看不到乞丐,已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地步。”[19]另有研究者指出,“蒋经国统治时期,政府‘集权式乡村动员体制’在赣南初步形成。政府前所未有地控制乡村的民众资源的同时,也承担起乡村社区的一切事务。从修路造桥、兴修水利、发展教育,到社会救济、家族生活、婚丧嫁娶,乃至乡人召伶演戏等等琐碎事务,政府一一插足,加以干涉。”[20]
尽管如此,大批潮汕难民前来,仍带来很大困难。“在泰和南门外河滩上定居之潮州难民达千余户,与赣北难民一二千户比邻而居。民国32年痢疾、霍乱猖獗,该地区死亡人数极多,每日病亡者,几皆为潮州难民。赣北难民被传染及死亡者甚少。尽由于营养良否、影响抵抗力强弱故也。”[21]又,“江西劳力缺乏,荒芜田地极多,谋生沿属容易,但难民人地生疏,语言隔阂,仍不免遭遇种种困难,但又必须及时就地寻求糊口。有不少难民以采伐山野柴薪为生,不免侵及有主之物,又有少数受生活所迫,穷取本地田野农产充饥。自亦有少数败类发生不检行为,时常引发纠纷。幸泰和一带人民极为善良,少有发生武力冲突事件,但对难民侵犯权益,仍不免深恶痛绝。本地人对外来人本易有成见,况语言隔阂,不易互相了解,建立感情。一旦有少数难民行为不检,更使本地人以偏概全,对所有难民均怀敌视态度,增加难民处境困难。”[22]
潮汕移民进入客区,涉及到潮客关系问题,不同族群相外,会出现对立、冲突,或是融合、转化。
客家民系作为汉民族的重要分支,已得到公认,然而关于客家人的定义,至今仍没有一个公认的统一标准。本文采用谢重光的看法,“客家民系是一个文化的概念,而不是种族的概念。使客家人与其他民系或其他族群相区别的完全是文化的因素,而非种族的因素。……客家民系在南宋初步形成以后,元明两代又有重大发展,约略至明中叶,其分布格局才基酊稳定下来,其独特方言、独特风俗、独特社会心理及族群性格才充分发展成熟。”[23]潮汕移民的由潮转客,最重要标志在于潮语为客语取代。潮汕族群和客家族群有很大不同,两者的转化不一定容易。而历史上进入客区的潮汕人,很多选择回到潮汕。抗战结束后,一些潮汕人选择回归和他们不太适应客家地区的心理有很大关系。
闽西的上杭、武平、永定、长汀、连城被列入纯客县,即客家人占绝大多数,即便如此,仍存有两个方言岛,位于武平的“军家语”方言岛和位于永定的非纯正闽南语方言岛。调查没有发现潮汕语方言岛,可证历史上移入的潮汕人彻底客家化。
再看江西情况。根据罗香林先生1933年统计的客家人分布情况,江西省有纯客住县10个,包括寻乌和安远,非纯客住县17个,包括赣县、兴国、瑞金和泰和。这是学术界对包括江西在内的客家人分布的第一次较全面的介绍。吴福文在此基础上,结合个人的调查资料,认为江西省有纯客住县市18个,包括赣县、兴国、瑞金,非纯客县有20个,泰和列入。[24]吴福文在罗香林之后,按理比罗香林更为准确,统计的纯客县增加7个,可能是非客家人被客家人同化的结果。按照吴福文的调查,入迁赣县、兴国的福佬人(包括潮汕人)早被客家人同化。
泰和县的情况较为特殊,据称现在还有不少潮汕人后代,形成江西地区罕见的潮汕人方言岛:
今天定居在泰和的潮汕人总数已达到十几万之多,他们的后代至今还讲潮汕话,泡工夫茶,甚至吃海鲜,乡音不改。当年,杨林斯的祖父带着杨林斯的父亲两兄弟从揭阳桐坑出发,一路跋涉,来到泰和占村落脚。距离林场不远的地方,就是占村,占村的居民,像杨林斯一样,几乎全都是当年的潮汕难民后代。生活在江西泰和的这些潮汕人,大多还保持着与潮汕老家的联系。当年虽然是躲避战乱、饥荒才来到泰和,但这些潮汕人很快适应新环境。懂得抱团取暖,则让他们形成独特的聚落,并从始至终保持着自己的语言和生活小习惯。[25]
泰和县马市镇占村,国内少数几个外地“广东村”之一,全村人几乎都是祖籍广东,主要是潮汕人和客家人,保持着纯正的广东味,包括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等。很难想象,在井冈山脚下的江西中部小县城泰和,居然生活着十几万广东移民及其后裔,约占其总人口的五分之一。[26]
为何泰和县出现潮语方言岛,赣州、闽西却不能,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笔者列举如下几个理由,以供参考:
第一,赣州、闽西是客家人的大本营,也是客家人的密集区,这里基本是纯家县,客家人占人口绝大部分,客家文化影响大,外来的非客家人口易被同化。
第二,进入赣州、闽西逃荒的潮汕人可以说漫无目的,没明确目的地意识,走到哪里就是哪里。赣州、闽西又是地域广阔区域,移入潮汕人比较分散,没形成潮语村落。并且移入的潮汕人并非以宗族形式进行移民,他们是国难时期的,没法在当地取得强势地位,易被客家人同化。
第三,逃荒的潮汕人不少是小孩、妇女,小孩本身没有族群意识,小孩往往被客家人收养,而妇女一般文化低,她们不少嫁给当地客家人。小孩、妇女极易被客家人同化,甚至很快丧失潮语交流能力。
第四,逃荒至赣州、闽西的潮汕人和地方客家相处较为融洽。固然他们刚到客区,遇到一些敌对心理和行为是可能的,但潮汕人慢慢被地方客家人接受、认可。潮客对立情绪低,有利于潮客族群融合。在此对比闽西客区的两个非客家方言岛,分别位于武平和永定,前者说“军家话”,后者操不纯正的闽南话,两个非客家方言岛之所以长期存在,和历史上非客家人、客家人在该地区的严重对立有关。
在弄清赣州、闽西没法形成潮语方言岛的原因后,再来看为何泰和县会形成潮语方言岛:
首先,泰和地属吉安市,在赣州北部,如果说赣州几乎是纯客住县区域,吉安地区就是各种方言区错杂之地。吉安地区客家人的力量远较赣州弱,无论是人口数量、客家文化或客家意识,泰和可列入非纯客住县,正是因为处于多种方言错杂地区,潮汕方言岛反而得以保留下来,而不易被客家方言区“吃掉”。
其次,泰和的入迁潮汕人很多,据说曾经超过十万人。据笔者所知,抗战时期,因大批移民进入而形成方言岛的还有兴宁和梅县,后两个地方也是大批潮汕人临时迁入的地方。但因为兴宁、梅县是客家人最强势区域,兴宁、梅县的潮语方言岛还是最终被客家方言区同化。
再次,战时江西泰和组织粤东难民互助,成立江西省粤东难民互助社,该社为难民做了大量工作,如协助开垦荒地、介绍职业、协助官方的江西省粤东难民救济委员会办理救济工作,协助难民丧葬事项,调解难民与本地人纠纷,调解难民内部纠纷,等等。[27]难民互助组织也有利潮汕难民的力结。
然而,泰和的潮汕人,在当地认为是“广东祖江西人”,对他们本身来说,在族群身份上有一些困惑。跟着时间流逝,估计泰和的潮汕人方言岛会迟早消失。
潮汕人进入赣南、闽西曾是历史上引人注目的现象,特别是抗战后期的移民逃荒,然而,长期以来,一般潮汕民众不太说到这件事。笔者本人是土生土长潮汕人,出生于饶平县黄冈镇,小时也极少听地方老人谈起,可是,饶平县在1943—1944年旱灾时期,据称饿死人数达到约八万人,整个潮汕饿死人数超过五十万!笔者对赣南、闽西的移民潮的注意,既和本人出身历史专业有关,也和自己最喜欢旅游,经常到客家地区游览有关。早在几年前,笔者协助编辑《潮汕史稿》一书的民国部分编写,第一次注意到抗战时期潮汕的难民潮。这几年来,通过汕头电视台的努力,慢慢的变多的潮汕人明白历史上有“走日本”这回事。赣南、闽西的潮汕难民潮长期受忽视,其解释原因有:
第一,战争时期,人命微浅。抗战时的潮汕饥荒,只是当时中国社会惨象的一个例子,就如太平天国时期华北出现旱灾,1918年一战结束欧洲流行瘟疫,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年潮汕出现大水灾受到忽视一样,战争或内乱大大削减人类对于战争时期疾病、瘟疫、水灾和旱灾的注意力。“时抗日战争已历数年,大家对灾难死亡的消息,已属空见,并未引起国人太大的注意;况斯时潮州大部分土地已沦入敌军铁蹄之下,亦可以说是无能为力。”[28]抗战结束不久,中国发生内战。1949年后,接连有“三反”、“五反”、“”、“人民公社化”、“四清”和“文革”等运动。连续多年的社会动荡严重削弱对抗战时期的潮汕难民的注意力。毕竟在战争、内乱时期,中国人的生命犹如蚂蚁一样不值钱。
第二,抗战时期逃难至赣南、闽西客区的潮汕人,多是普通平民,这些人一般没有深厚社会背景。以往潮汕人对于香港、台湾和海外潮汕人比较关注,但关注对象不外乎是发财的富商大贾,他们引领国内外经济发展,即所谓“成功人士”。即使是学术界针对香港、台湾和海外的研究,针对普通潮汕人的研究也是不多的。从研究角度看,抗日战争的潮汕移民研究属于社会史、人口史的领域,较多依赖口述史料和人类学、社会学调查,传统潮汕文化的研究者以文史爱好者为主体,他们主要是根据文献资料做研究,所受学术训练有所欠缺。一种原因是针对平民研究视角缺失,一种原因是研究者“心有余而力不足”,导致以往学术界对赣南、闽西的潮汕移民关注不够。
——本文载于《广东史志》,作者陈雪峰,中大史学硕士,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广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如需引用本文,请以纸质媒体为主。
[2]李文生、张鸿祥著:《客家首府:汀州揽胜》,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7—8页
[3]李文生、张鸿祥著:《客家首府:汀州揽胜》,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8页
[4]施奕群主编:《潮州商业志》,潮州市商业局编印,1988年,第375—378页
[5]梁小民著:《走马看商帮》,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第144页
[6]潮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潮阳县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80页
[7]温锡浩:《序言》,政协福建省龙岩市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等编:《闽粤一江亲:闽西抗日战争中的潮汕难民》,厦门:鹭江出版社,2015年,第1页
[8]江初炘:《福建连城庙前潮汕难民小志》,政协福建省龙岩市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等编:《闽粤一江亲:闽西抗日战争中的潮汕难民》,厦门:鹭江出版社,2015年,第289页
[9]江初炘:《福建连城庙前潮汕难民小志》,政协福建省龙岩市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等编:《闽粤一江亲:闽西抗日战争中的潮汕难民》,厦门:鹭江出版社,2015年,第290页
[10]《山水迢迢逃难路》,汕头电视台“梦归潮汕”栏目第三十六期节目,2018年11月11日
[11]陈荣华等著:《江西经济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29页
[12]谢重光著:《福建客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35页
[13]葛剑雄著:《中国移民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81页
[14]葛剑雄著:《中国移民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86页
[15]沈耀奎:《潮州饥民就食江西之回忆》,政协福建省龙岩市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等编:《闽粤一江亲:闽西抗日战争中的潮汕难民》,厦门:鹭江出版社,2015年,第62页
[16]《马坡岭潮人纪事》,汕头电视台“梦归潮汕”栏目第十二期节目,2018年5月20日
[17]沈耀奎:《潮州饥民就食江西之回忆》,政协福建省龙岩市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等编:《闽粤一江亲:闽西抗日战争中的潮汕难民》,厦门:鹭江出版社,2015年,第62页
[18]聂志刚:《抗战时期江西省临时省会泰和回顾》,《江西文献》第222期,2011年2月,第14页
[19]黄嘉焕:《抗战时的赣州》,《江西文献》第113期,1983年7月,第32页
[20]黎志辉:《蒋经国“赣南新政”时期的社会动员》,《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4期,第51页
[21]沈耀奎:《潮州饥民就食江西之回忆》,政协福建省龙岩市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等编:《闽粤一江亲:闽西抗日战争中的潮汕难民》,厦门:鹭江出版社,2015年,第63页
[22]沈耀奎:《潮州饥民就食江西之回忆》,政协福建省龙岩市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等编:《闽粤一江亲:闽西抗日战争中的潮汕难民》,厦门:鹭江出版社,2015年,第63页
[23]谢重光著:《福建客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页
[24]周建新等著:《江西客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6页
[25]《井冈山边潮州村》,汕头电视台“梦归潮汕”栏目第九期节目,2018年4月29日
[27]沈耀奎:《潮州饥民就食江西之回忆》,政协福建省龙岩市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等编:《闽粤一江亲:闽西抗日战争中的潮汕难民》,厦门:鹭江出版社,2015年,第67—73页
[28]沈耀奎:《潮州饥民就食江西之回忆》,政协福建省龙岩市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等编:《闽粤一江亲:闽西抗日战争中的潮汕难民》,厦门:鹭江出版社,2015年,第59页